
来自百济神州有限公司的副总裁、转化研究及转化医学负责人沈志荣博士作了题为《百济神州生物药研发及展望》的精彩报告。沈博士在报告中给出百济在产品开发方面清晰的思路。百济主要聚焦肿瘤及自免疾病,研发已经覆盖80%以上的肿瘤适应症,药物产品除了目前已有差异化的产品管线,也正在布局FIC靶点、新技术CDAC、BsAb/TsAb、ADC,未来也会布局pro-cytokine、细胞治疗CAR-NK和mRNA治疗领域。目前有50+项目在推进,预计2年内有10+项目进入临床。未来百济仍在不断探索和寻找新modality来调节免疫微环境,治疗癌症,一起推动中国医药产业发展。

来自北京理工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谢海燕教授作了题为《仿生免疫协同诊疗系统》的精彩报告。免疫治疗通过增强或抑制机体的免疫功能以达到治疗疾病的目的,适用于肿瘤、炎症等多种疾病,但目前还面临多重挑战。利用细胞膜仿生修饰的纳米材料有望根本上改变血液相容性并且赋予其独特的生物学功能。谢海燕教授的报告介绍了可特异识别CD8+DCs的可视化仿生纳米疫苗及人工抗原提呈细胞,能够很好的抑制肿瘤生长;将过继性NK细胞进行类囊体膜的工程化改造,建立兼具优异肿瘤杀伤和微环境调节作用的NK,在小鼠体内获得了高效的抑瘤效果。利用细胞膜仿生技术可以构建各异的仿生诊疗系统,为高效的肿瘤免疫诊疗提供新思路。

来自成都中科奥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创始人兼董事长潘登科博士作了题为《基因编辑小型猪在异种器官移植和人类疾病模型的产业转化》的精彩报告。猪的器官大小、解剖、生理生化、代谢与人类非常相似,是异种器官移植理想供体和人类疾病的理想模型。免疫排斥是异种器官移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随着基因编辑技术、体细胞克隆技术及新型免疫抑制剂(如CD40抗体)的突破,已基本克服这一问题,显著延长了受体存活时间,美国已在患者体内完成试验,并取得不错的结果。但仍存在急性、慢性排斥、生物安全及争议等问题等亟待解决。中科奥格培育了多种基因工程供体猪种系,开展了多项临床前试验,建立了高标准质控体系,医用猪有巨大的医学应用价值和疾病治疗前景。

来自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耳鼻喉研究院的副院长舒易来博士作了题为《耳聋基因编辑与基因治疗》的精彩报告。先天性耳聋的遗传因素约占60%,耳聋是单基因病。CRISPR/Cas9系统可以实现单碱基、RNA及Prime的编辑,在遗传性耳聋等遗传性疾病的精准治疗有广泛的应用前景。舒博士分享了利用基因敲除策略对Myo6显性遗传性耳聋小鼠的基因治疗研究,及基于同源修复对Klhl18lowf隐性遗耳聋小鼠的基因治疗研究。对后天性耳聋,例如药物损伤,可以通过基因编辑系统对HtrA2进行敲除,该模型可以抵御新霉素药物引起的听力损失,且没有明显脱靶。
Panel3:新概念、新技术和新方法将如何助力临床需求的满足

四位嘉宾精彩的报告结束后,由云顶国际副总经理郭朝设博士主持,围绕新概念、新技术和新方法将如何助力临床需求的满足等热点问题和观众朋友们的提问,与三位嘉宾进行了一场热烈的讨论。
沈志荣博士
Q:百济在靶点创新、技术平台及成药形式上是怎么选择的?另外对全新靶点或者全新分子比如双抗、ADC等在研发尤其是临床转化方面百济主要考虑的要点有哪些?如何尽可能减少或者避免不确定性,提高成功率?
A:从我自己个人的角度说一些我的看法。像PD-1等靶点或者是技术平台、成药性等方面怎么去考虑,无论是已经验证的靶点或者是创新的观念,我觉得归根结底是解决临床问题。泽布替尼是一个选择性、安全性特别好的BTK抑制剂,不仅仅是中国第一个出海的新药,它在临床上也做出了头对头特别好的疗效,解决了很大一部分患者的问题。所以归根结底是怎么去解决这些临床上的需求?
最终有两类,第一类是有POC(proof-of-concept,临床概念验证)的靶点。我们会去想能不能做一个更好的药物,去解决它的安全性问题、耐药或者是毒性等已有药物没有解决的问题,使它成为一个Best-in-Class(BIC)新药。第二类是大家经常说的First-in-Class(FIC),没有POC的药物靶点。这个时候我觉得非常考验的是团队的科学判断。因为没有临床数据验证,那么从Scientific mechanism的角度是不是make sense。假设药物做出来能不能解决一部分的需求。我觉得从这两个方面进行考量。总体来说,做创新靶点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关于技术平台,归根结底是由需求驱动的,但需求是由目标驱动的。假如要做一个BIC的ADC,需要linker、payload,需要选一个好的抗体,这时候不得不去根据某一个靶点选择合适的平台进行开发,最终看能不能做出一个BIC药物。所以我觉得平台最终是由目标、由需求来驱动。比方说,做CAR-NK等细胞治疗,到底用什么样的技术平台去驱动产品开发?技术平台可能就像是武侠里面的内功,产品是招式。招式是打拳,内功决定了拳打出来有没有威力。
成药形式更加需要科学和临床驱动两方面的考量。比方说,有很多tumour-antigen的抗体最后是做成T cell engager、NK engager、ADC、CAR-NK还是CAR-T,需要看competitor landscape有没有需求。比如,临床上有20个ADC在研,再去做一个ADC,有没有这个需求?也许有。举一个例子——HER-2,DS8201a今年的ASCO大放异彩。HER-2做了很多年,ADC也做了很多年,依然还是有问题可以去解决。
第二个点,Scientific mechanism能不能justify去做一个新的modality。比方说,在领域里走在前面的药物是ADC,那ADC用完之后,病人是用T cell engager还是用NK engager或CAR-NK好呢。也许一开始没有答案,需要进一步试验判断看到底哪一个mechanism能更好地解决这部分病人的问题。关于不确定性的问题,做新药肯定都有不确定性。我觉得最终可能是有POC和没有POC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做好portfolio的Balance,减少不确定性。
Q:百济神州的在研管线和技术平台,您最喜欢哪一个?
A: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各有各的好处。现在要说喜欢哪一个,我认为就是在描述哪一类让你觉得exciting。比方说,PD-1在三期临床很多都已经获批了,你知道它很好,它会不断的往前走。然后在临床前还没有进临床时,我觉得在Phase 1阶段是最exciting的,因为这个时候临床试验在不断进行,数据在不断的产出。
我们做转化研究,看基因表达、免疫组化、靶点等因素与药物疗效的相关性去做出判断。
我觉得有几个判断。一个判断,这个药到底行不行,到底有没有疗效,这个signal是不是真的有疗效,将来有没有更大的前途,未来能不能走向注册、三期临床,会不会获批。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同时又需要你的科学判断。而且这个数据在不断的更新,临床前到临床转化的过程中会不断的发生改变。比方说,第一个,我们现在有差异化的OX40抗体,是一个潜在的FIC,抗体不竞争OX40与OX40L的结合,抑制OX40在Tregs表达,有两个MOA,在开发过程中可以不断的去检验你的idea。第二个,我们有HPK1, 可以去激活T细胞,可以跟各种免疫激活进行联合。第三个,现在大家经常讲的PROTAC蛋白降解技术。follow我们前面走得最快的泽布替尼,我们的第一款PROTAC-BTK PROTAC已经进入了临床。药物开发过程中数据会不断update然后去做分析,有新的数据出来的时候是最exciting的。
Q:针对同一个适应症,百济的不同药物管线/不同疗法是怎么选择推进的呢?
A:这些问题其实都是我们经常说的转化研究和转化医学的问题,尤其是大家经常问转化研究和转化医学能用来干什么。从2015年开始做创新药开始,国内早期是不太做的。为什么呢?以前做仿制药或者做me-too的药物,基本上选原来的靶点的适应症就行了。但是随着做BIC或者FIC,从临床前到临床的过程中,有大量的转化的问题需要去回答,其中就包括适应症的选择和组合的调配。临床中还有很多其他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如何选择dose。尤其是对肿瘤免疫治疗,选择什么样的剂量是怎么定的。第二个问题,怎么选靶点,怎么选适应症。免疫检查点靶点如何去选择适应症,这中间有很多科学的问题存在。
适应症里同样的drug和不同的drug在同样的适应症里,如何去选择?我觉得最后要根据靶点的抗体或者是小分子药物在Phase1/2已经表现出来的data和对整个适应症的landscape变化去进行判断。比如两个抗体target不同靶点,是联用或单用来与标准疗法对比,还是一个药物与现有标准疗法联用?归根结底是一个转化的问题。需要在早期尤其是新药Phase1/2的临床实验中去理解药物的mechanism,对它可能的疗效作出判断。
同时在临床前,大动物肿瘤模型以及自发的肿瘤模型等可以在real tumor环境去研究转化医学的问题,还可以做PDO、PDXO包括一些原位的肿瘤模型,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它可以达到一个最大的免疫激活,这可能帮助你选择合适的一个组合进入临床去进行探索。
另外,最终我觉得是在不同的适应症上细分人群的工作。将来在不同的实体瘤里面会越分越细,当不断细分的过程中,这些抗体、小分子等药物各自能够适用的人群就逐渐地被细分出来,达到对患者最大的获益。在那一段时间的标准治疗下,它的疗效是最好的。
虽然大家经常讲精准医学,但可以看到真正伴随诊断的开发还有long way to go。在国内,6月28日国家药监局医疗器械技术审评中心发布《与抗肿瘤药物同步研发的原研伴随诊断试剂临床试验注册审查指导原则》。将来,我认为这些tumor-antigen会把所有的肿瘤分成非常多的细分的segment。对药物开发而言,不论是小分子还是抗体将来要去compete各自segment里面最好的药物。这也是一个出海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如果要在某一个人群里面去跟它compete,它的患者人群是用什么方法鉴定出来的,你能不能用、有没有权限去用,这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将来诊断试剂或者方法可能也会成为企业的护城河。
总结来说,选择适应症是需要多方考量的:mechanism和landscape,一线是与化疗对比还是单药,这中间有很多的balance要去考虑。
潘登科博士
Q:就像您报告讲到的,今年报道世界首例猪心移植引起了广泛关注,也显示了异种器官移植的可行性,不幸的是患者在接受移植后2个月去世了,尽管有媒体报道称猪巨细胞病毒感染可能是主要诱发因素,但最近相关的科学团队在NEJM发表了详细的研究分析结果,借此机会请您从更专业的角度进一步解读一下这篇文章以及其它可能导致病人去世的原因,以及在以后类似临床试验中如何克服或者避免,从而提高成功率和病人的生存期与生活质量?
A: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确定用猪做为异种器官移植的供体,经过30多年的研究,这次将猪的心脏移植给人存活了两个月,是国际研究者公认的、跨时代的里程碑。有些人认为存活两个月是失败的,但正因为有了这次的试验,近期美国已有三家医院计划开展异种肾移植临床实验。回顾人类历史第一例人与人的器官移植,存活时间18天。异种移植60天已经是很大的进步了,但这还远远不够,未来进入临床,我们希望存活时间在1-2年以上。关于郭博士提到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造成的。
首先,病人状况不好。病人的依从性,包括遵医嘱等方面不好。病人十几年前做过心脏瓣膜手术,吃过很多药。这次做心脏移植之前病人处于急救状态,且患有血小板减少症、心律衰竭、高血压等一系列疾病,向美国四个地区的十几家医院申请器官移植,都没有获得批准。在此基础上进行异种移植且存活两个月,时间上还是比较长的。我个人推测如果是一个状态更好的病人,早期进行移植,可能存活时间能够达到半年、一年,甚至更久。
其次,急性排斥反应和病毒等原因。第一,急性排斥反应。虽然文章中提到没有典型的人与人之间的急性排斥反应,但还是存在异种移植之间非典型的急性排斥,这也是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第二,病毒。后期检测到供体猪脾脏有巨细胞病毒的存在,但这一问题可通过净化设施进行解决。基于此美国正在推进异种肾移植临床实验。
Q:如果在中国进行类似的临床试验,技术上与监管上主要还面临哪些要解决的问题?依您的判断,中国异种器官移植在今后5年、10年会有哪些里程碑研究或者应用上的突破?
A:在技术上,我们和美国有一定差距,美国做了二十几年的研究,中国是最近五六年时间。基因改造猪方面,我们和国外差距很小,国外是十基因猪,国内也拿到了六基因猪。我们最大的差距是猪到猴的研究以及医院合作,需要更多研究人员的加入和认可,我们的猪猴实验在规模和数量上与国外相比存在较大差距,我们三年完成了30例,但美国一年就能完成40-50例。二是开发新型免疫抑制剂,美国的抗CD40抗体在异种移植中取得了突出效果,而在国内很难获取该抗体。
在监管上,第一,我们一直在跟有关部门沟通。第二,异种移植审批路径是否按照药物需要进行一期二期三期。事实上根据国外及与行业各专家沟通,异种移植应该先按照细胞治疗形式进行审批。通过医院备案,卫健委、伦理等报备,跟随学习美国的相关政策。美国2016年更新了器官移植供体猪的来源、内源性逆转录病毒的要求、病原微生物的要求。我们希望未来,我国从国家的立项还有监管上都有规划进行。现在行业内有院士在推动相关法规,我们也在做供体猪的标准,参照药物生产的标准,严格把控质量,已立项了四项行业标准。。
希望未来中国能够三年左右追上美国,五年进入临床应用,十年进入大规模的商业应用。
Q:技术上目前我们最多的是10基因敲除猪,是否能够满足现在异种移植的要求?这方面还要进行哪些探索?之后是否会增加基因敲除数量?
A:猪对于人存在许多异种抗原,这是引发免疫排斥的根本原因,目前国际上公认的是三个主要异种抗原,无论是大家提到的10基因敲除猪还是13基因敲除猪,均敲除了这三种抗原,此外,就是转入人源免疫调节和保护基因来增加移植物在受体内的兼容性。为了让器官变小而敲除的生长激素因子,这不是主要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是异种抗原,可能还会发现第四个比较要的抗原,进一步降低移植后的急性排斥反应。现在FDA的要求是,不是基因修饰的越多越好,基因修饰的总原则是越少越好。将来可能七、八个基因更好,也可能十一、二个基因更好,优化基因组合和表达效果是未来非常重要的方向。
未来可能会增加1~2个抗原的去除,目前大家较为关注的包括:猪的SLA抗原以及发现新抗原。还要将免疫方案、免疫耐受等技术结合起来,而不是追求基因修饰越多越好。
舒易来博士
Q:从技术上讲,针对小鼠基因组序列的gRNA可能不一定适用于人体,您们在做gRNA筛选中是只是针对小鼠基因组的编辑还是找到能识别人基因组的保守序列? 在临床转化上CRISPR的脱靶问题怎么解决?小鼠和人体在耳聋结构等方面相似性多大?有没有技术上的差异性?
A:耳聋领域和眼睛类似,它是相对比较独立的一个器官,一般进行局部注射给药。我们目前在小鼠模型上来做的sgRNA都是WORK的。因为遗传性疾病主要分为显性和隐性,我们都是选择一些相对比较常见的、比较热点的突变,在小鼠上证明它是WORK。转化到人身上,如果保守的,sgRNA是可以直接去尝试的;如果不保守的,sgRNA需要重新再做一次筛选。我们在其中一种基因上做了重新筛选,发现对人也是WORK的。但是出于有效性和安全性的考虑,真正用到人身上还是要进行一个系统的筛选。
脱靶是基因编辑很常规的一个问题,我们现在用的是基因编辑的敲除策略和单碱基编辑。随着基因编辑技术的提高,也会更加带动基因治疗领域。我们现在在用RNA基因编辑的方法进行合作,它是非改变DNA的编辑,相对安全性可能会更高。我们现在一直在探索更好的基因编辑方式。当然,既要考虑有效性,也要考虑安全性,尽可能避免脱靶。
关于要实现转化的门槛,第一方面,最好是能实现AAV的特异启动子,才更安全。第二方面, AAV的质量、质控还需要进一步提高。
先天性耳聋为什么发病率高?因为耳聋不致死,耳聋基因会一代一代传下去。耳聋病人完全不会影响到生殖。耳聋基因有筛查显示人群的携带率有15%。耳聋技术指导组的一个多中心的筛查证明携带率是15%。黄院士的团队进行携带者筛查,前十个基因有两个是耳聋基因。
但是其实耳聋在儿童中会引起聋哑,聋哑人耳聋是完全不会讲话的。聋哑发病率很高有15%,夫妻之间是相同基因就有几率生出的小孩儿是一个聋儿。另外,耳聋基因现在被证实绝大部分都是单基因病,一个基因突变就会引起耳聋。在耳聋的基因治疗方面,这几年发展还是很快的,包括美国和中国很快都会进入临床 。将来也会做出基因治疗药物让耳聋病人能够恢复自然声音。
感谢报告嘉宾的精彩分享和交流探讨,部分报告内容会在云顶国际直播间继续开放,点击链接:https://to.plvideo.cn/mix/101966即可观看。云顶国际将继续为大家建立自由、高效的分享交流平台,期待明年海门再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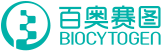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1502005564号
京公网安备: 11011502005564号